店铺起名诗(店铺起名诗经)
梅兰芳说:“作为一名好的演员,离不开鼓师、琴师和化妆师。”
在梅兰芳长达半个世纪的舞台生活中,为他伴奏的共有三位琴师,徐兰沅、王少卿、姜凤山。
徐兰沅自1921年开始为梅兰芳操琴,两人合作了28年。他为梅兰芳排演新戏、创造新腔,促进了京剧音乐的发展,后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解放前就已颐养天年。
王少卿系老生名家王凤卿之子、“通天教主”王瑶卿之侄,在伴奏乐器中增加二胡由他创始,此举丰富了京剧乐队的表现手段,为京腔京韵增添了新的色彩,他与梅兰芳合作了33年。
姜凤山为梅兰芳操琴的时间,集中在解放以后。梅兰芳为庆祝建国十周年而排演的献礼剧目《穆桂英挂帅》,其唱腔设计就是出自他手,他和梅兰芳合作了12年。
姜凤山口述/任秀丽(红袖)整理
1923年九月初一,我出生在北京。小名叫进才,三叔的孩子叫进宝,那会儿不是穷嘛。
加入文林社带艺学戏时,叫姜文亭;嗓子倒仓了改拉胡琴,叫姜凤山;小嗓子喊出来以后开始唱旦角了,叫姜桐秋;不唱戏了又拉起了胡琴,又改叫姜凤山。那时随意,现在改个名字难着呢。
我家住在崇文门外手帕胡同54号,侯喜瑞也住在这个胡同。我家租住的四合院有三层,父母和我住在第三层。
我的父母是光绪年间出生的人,母亲是旗人,正黄旗。我舅舅在宫里当差,吃俸禄。姨兄姨弟见面时互相请安,就像老舍在《茶馆》里写的那样。
到了中华民国,皇帝没了,俸禄也就没有了。坐吃山空,家里的积蓄慢慢地也就花完了。
我父亲磨起了眼镜,给大明眼镜公司磨。磨眼镜很苦,全靠人工操作,脚踩着凳子,身边是砣子和砂子,因为胳膊肘老贴着干活,被磨得全是茧子。眼镜磨好了,就给大明眼镜公司送去,等于是它的工人。活虽然苦,可也挣不了几个,一副眼镜也就一百、二百的,靠这个维持生活。
我家是外行,在戏班里没亲戚。
7岁时,我在手帕胡同上私塾,不爱读书,老逃学。手帕胡同里,就是英子胡同,英子胡同有个茶馆,茶馆里有个票房叫“和声雅韵”,我就站门口听。我爱听花脸,就偷学了一出《托兆碰碑》。
票房里有个票友叫关鸿斌,见我老去,就问我:“敢不敢唱?”我说:“敢唱。”就上去唱了。唱完后关先生问:“跟谁学的?”“是从您那儿偷学的。”
我有个干爹,是父亲的磕头把兄弟,叫王福亭,他是个戏迷,跟叶春善(富连成班主)要好,常常带我去看富连成的戏。
8岁那年,我考过富连成,萧长华瞧我长得眉清目秀的,就说:“你唱青衣。”我问:“什么叫青衣?”“就来小媳妇的那个,来娘娘的那个。”“不唱,我要唱花脸。”
关先生后来拜了侯喜瑞。侯喜瑞,架子花,靴子底三寸厚,坡度大,人穿上显得瘦溜、精神。论扮相,他的脸谱在花脸中更好看。嗓子有炸音,有气势,人称“活张飞”、“活曹操”,可有一出曹操戏他不唱,《逍遥津》(《白逼宫》)总是让蒋少奎替他。
关先生也给我找了个老师李福庆。那时拜师很简单,家里弄点小菜,喝点酒,磕个头,就算拜师了。之一出,说的是昆曲《芦花荡》,唱张飞。学了一年多,学了几出架子戏。
除了跟李福庆学,还去侯喜瑞家,侯先生先给关先生说戏,我看着,关先生再给我说。
光学戏不行,得登台唱戏,之一场戏是在广兴园唱的,还是《托兆碰碑》,老生是凤志鸿,高派。
1933年我10岁,在关先生的帮助下进了文林社,改名姜文亭(“文”字辈),带艺学戏。练功的时候,我比别的孩子溜,旋子能翻20多个。那时候,不懂什么叫苦,就知道练功,将来能养家糊口,能成好角儿,没别的想法。
那时候练功不看钟表,点一炷香,隔一寸画一道杠,杠到了,就换一个练。
开始是拿顶,拿完顶下来,活动活动腰,走走圆场,然后耗山膀,耗山膀也练腿上的功夫。看功老师是诸连顺,诸先生个子不高,不爱说话,拿着刀劈子站在旁边。
耗着耗着,胳臂肘就酸了,就开始耷拉,就要往下放。见你前弓后蹲,“啪!”的一声,诸先生的刀劈子就下来了,不带说话的,“啪!”“啪!”打 *** ——不是有“打戏”这一说吗?有钱的人不学戏,穷孩子才学戏,好有口饭吃。
接着耗腿,也叫撕腿,靠着墙根儿坐在地下,把两腿撕开,撕得跟墙一般平。撕完了腿,起不来了,老师就按着大筋搀着你起来,让你蹲一会儿再起来跑步,活动活动大筋。
然后踢腿,左右腿,前后踢,踢月亮门,现在叫武功课。
踢腿完了翻跟斗,从虎跳开始,前小翻、鹞子、旋子等等,这叫毯子功,名义上叫毯子,其实没有毯子,就在地上铺块布。
我没有因为练功受过伤,可能是 *** 比较科学:练腰的时候,老师让你躺在他腿上,揉胸、揉腿;翻跟头的时候,用腰带兜着你;告诉你在台上演武戏的时候,不能犹豫,脑袋不能抬,不能张大嘴,眼睛要平看。
毯子功练完了,练把子功,先练枪,小五套,后练大刀,然后练对打,大刀和双刀,大刀和枪,刀下场、枪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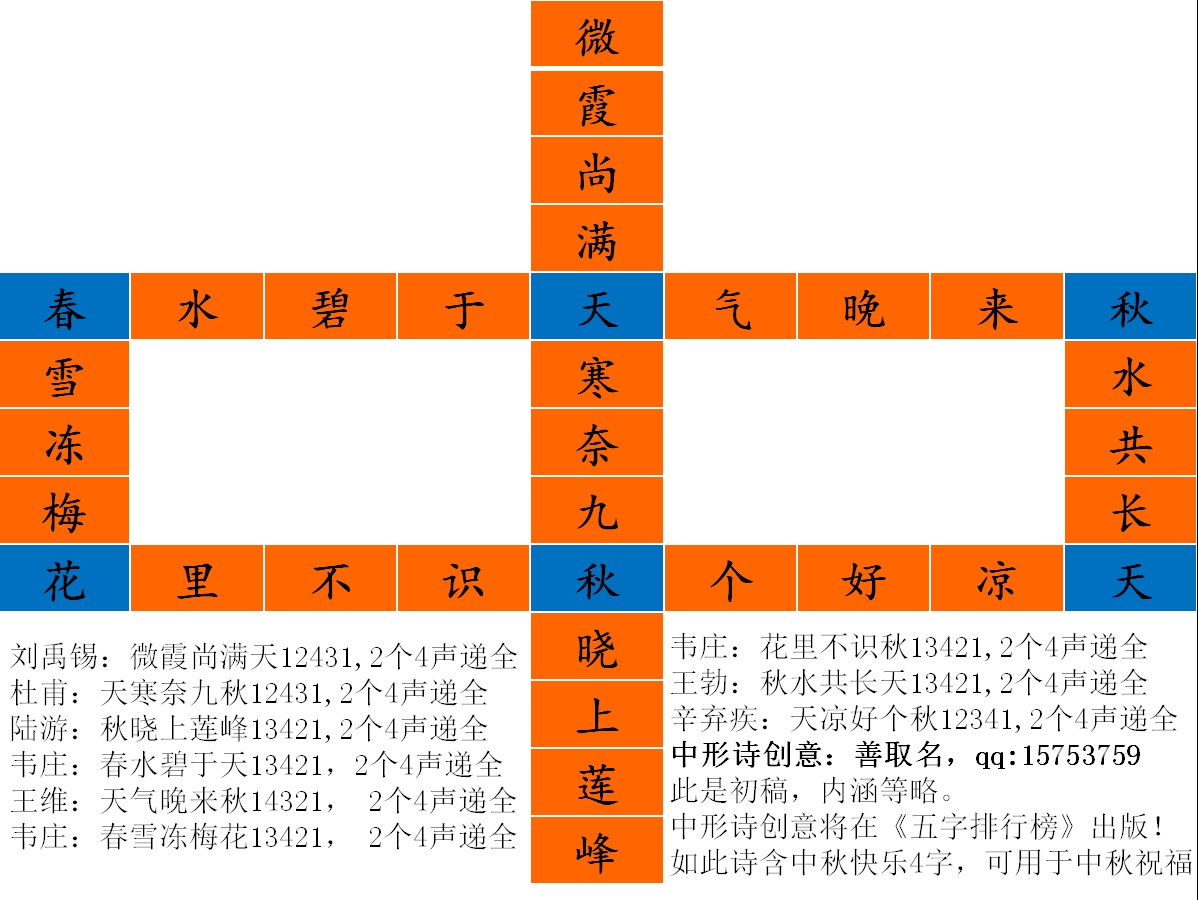
把子功练完了,练马趟子。
马趟子练完了,拉胡琴的师傅就来了,开始吊嗓子,老师拿戒方,拍着板,唱不好打手,嘴张不开胡噜嘴。
吊完嗓子,就被叫到屋里说戏,十几个人站在炕头。说的戏多了,《草桥关》、《白良关》、《太平桥》、《下河东》、《御果园》……
学会了就唱,学生唱戏没有戏单,就是海报,当街一贴:在哪演出,演什么戏。在科班,我那花脸,搁现在叫尖子。除了我,还有田文芳(旦角)、张文麟(老生)和张文麒(武生),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两大枚,现在叫津贴、补助金。科班管饭,吃的是官中饭,除了馒头就是米饭,菜也就那样。老师发给我们两大枚,就是增加补助,拿它能买一大枚烙饼和一大枚酱肉,吃得挺好的。
我学的是金派,金少山有戏,虽说不能场场必到,可老去听。
头一回,在华乐戏园(后改名大众剧场),《取洛阳》。勾马武的脸来不及了,他就把膛子先画出来,把绿脸勾上膛,勾个大概齐,唱一场下来再补齐。岑彭有一句唱:“腰中常挂三尺剑……”
他接了一声“哈嘿”,声音跟雷一样,嗓子大啊。个子又高,扮相漂亮。
有一回,在广和楼,他脚崴了,唱不了了,舞台上就戳出一个牌子:“金艺员因脚受伤,不宜登场,请诸君原谅。”他唱一出戏,前头且得加场子呢。观众知道他经常泡蘑菇,不答应,见不到人不行,见到了才心满意足。经励科到他家去请:“戏回不了,都等着您呢,唱几句就行!”到后台,先得喝碗豆腐脑,广和白家的,白博士的豆腐脑,还得多放辣椒油。一边喝一边勾着脸,有人给他穿靴子、披胖袄。那天唱的是《草桥关》,前面的戏他都没上,只唱了一场“万花亭”。两个“太监”搀着他上,他的脚瘸着,一共才唱了12句,可台底下这个叫好声啊。
广和楼在肉市那个胡同,左边就是前门大街。他唱戏的时候,你上前门大街听听,准听得见,尤其《连环套》里的那句“洋洋得意呀……”就这个声音传到前门大街,黄钟大吕啊!那会儿的剧场不像现在这么严密,四面都是窗户,隔不住声音。
也看杨小楼的戏,他当初学花脸。看他的戏,比方《霸王别姬》、《连环套》,我就觉着:亮相怎么那么威武,那劲儿。
金少山和杨小楼,这两个霸王,都是好霸王。看他们扮什么样儿,扎什么靠,怎么出场。
还有孙毓堃、刘宗杨这几个武生的戏,我也看。
杨小楼跟孙毓堃,这两人的《挑滑车》,没人这么扮。
孙毓堃的高宠,起霸时靠牌子冲台下、里靠冲外,看着很新鲜,提溜起来和别人不一样。之一次看到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
杨小楼的枪花特清楚,表示这枪很沉,翻身亮相就齐活。关公的大刀,高宠的大枪,霸王的大枪,不是随便耍出来的。还有李克用的大枪,九九八十一定唐刀。
杨小楼的《金钱豹》,有一场武打,是跟猴子,他抛叉,猴得接住,接着还得摔一髁子。那天在广和楼,这叉扔到了尽头,差点都快到观众那了。迟月亭来这猴,脚蹬栏杆,把叉夺了回来,没法甩髁子了,走了一身段,就着柱子一转身,上了柱子了,绝了。他没演过主角,都是傍角,来猴,来马童。专门配红花,他是好绿叶。
我的第二场戏,是在珠市口的开明戏院唱的,唱的是《空城计》,李慧芳的诸葛亮,我来司马懿,这是1934年的事。
1935年,梅兰芳在之一舞台(珠市口西边)唱《太真外传》,《太真外传》里面有一段翠盘舞,梅兰芳与姜妙香在翠盘上舞蹈,唱昆腔“赏花颂”,从1月唱到12月,12小童拿着花在翠盘边翻跟头。12小童是从各班社借的,文林社的有4个,张文麟、张文麒、田文芳和我。从那时起,我就与梅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6年,文林社上武汉和温州演出。在温州,有个资本家看中了我们这帮学生,就把文林社卖到温州了,我们就不能回家了。
远在北京的家长们,听到这个消息急了,我是独生子,像我这样的,还有好几个。
他们就去找梨园公会,梨园公会沈玉斌等负责人就去找梅兰芳:“好些小孩呢,怎么办?”梅兰芳就拿大洋把我们赎了回来。
赎回来以后,梨园公会会长沈玉斌领着我们这些学生,把梅兰芳请到梨园公会。大伙儿一起向梅兰芳道谢:“谢谢梅先生!”梅兰芳摸摸这个,又摸摸那个。
我们被赎回来了,文林社也散了,尚小云想接收这帮学生,创建荣春社,其他人都去了,教我的老师张鑫奎不让我去,他带着我在雷喜福、孙毓堃、刘宗杨等班社唱戏,外加给他做饭。
师娘搭背,动不了,老师抽大烟。两个师妹(小师妹张玉蓉后来嫁给了方荣翔)和一个师弟(叫小九)都还小,就挑上我,我也干净,绝 *** 脏衣服出门。
开始做的不好。
“先生,吃什么?”“吃烙饼吧。”
师娘说:“和面吧。”和来和去,和成面糊了。
先生问:“你没吃过烙饼?”“吃过,我妈烙的,我不会。”
师娘又让我往里面掺面,和好后,这面就多了。先生一看这面,就说了:“你这盆面,够我吃一个礼拜!”
后来回家跟我妈学和面、烙饼,三翻六转一提溜,学会了烙饼。又学炒菜,上饭馆吃饭,横盛馆、复兴楼(崇文门大街俩饭馆),我就偷看厨子怎么做菜。学了一道菜,先在自己家做,然后再给老师做,老师挺满意的:“你小子行啊!哪学的?”“偷学的。”
我不在老师家吃,回家吃。如果下午和晚上有戏,就买烧饼果子吃,也不回家睡觉,就在老师家里睡。老师家的堂屋供着祖师爷,我就在边上横俩凳子,铺块木板,在那上头睡觉。
散戏回去,老师抽大烟,叫我去贾家胡同口买冻柿子,老师爱吃冻柿子。天冷,我托着两个柿子跑着回来,手都冻僵了。把柿子拿水冲干净,切成片,给老师送去,然后又到院子里练功去。等我练完了功,老师也抽完大烟,也吃了柿子了,再给他熬粥去,等他吃完了夜宵,精神来了,有时还给我说戏,说完戏,又伺候他睡下。
第二天早上,4点半我就起床了,清扫厅堂,把中堂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去陶然亭练功、喊嗓子。
那时候,金少山也到陶然亭喊嗓子,拉着狗、抱着猴、架着鹰,王长林和周瑞安陪着。
金少山在陶然亭的一个茶馆里坐下,叫人沏上一壶好茶。隔着只有几百米,我们喊嗓子,他听得见,他就来了一句《御果园》里的“哗啦啦啦……”,全陶然亭的人都听见了,我们十来个一块儿喊,也没他这一条嗓子好,他的嗓子,绝了。
我在陶然亭喊完了嗓子练完了功,就会顺路买些吊炉烧饼和焦圈带回去。老师起来了,漱口水、洗脸水早就摆好了。他洗脸,外加吃早点,我开始拿顶。
上午练功、吊嗓子,下午开始唱戏,一个晚上跑两个剧场。
雷喜福有两个儿子,雷振春和雷振冬,雷振春拉胡琴,雷振冬是老生,我傍着他唱。
还有胡少安,他跟赵宝奎学戏,我也跟他一块唱过。
《捉放曹》、《阳平关》、《白马坡》、《牧虎关》都唱了,唱了有四五十出。
1937年,日本人侵占了北京。梅先生去了上海,不唱了。
梅先生1919年和1924年就去过日本,演过《天女散花》、《贵妃醉酒》、《洛神》等,轰动一时。他在日本的名气太大了。但侵略既成事实,梅先生决心已下。冯六爷(冯耿光,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跟梅先生见面,也赞同梅先生不再登台。医生上梅家去,给他打了一针。大家都知道梅先生病了,唱不了。
言慧珠继承了梅先生的《太真外传》。在徐兰沅、李春林的帮助下,在北京演出,用的是梅兰芳的班底,除王凤卿的唐明皇外,其余都是梅剧团的人。唐明皇是李世章,拉胡琴的是黄天麟,二胡是梁顺意。我也参加了,排戏的时候负点儿责。
《太真外传》一共四本,梅先生分四天唱完,慧珠改成一天唱两本,两天唱完四本。
我在大班唱了3年,唱到16岁,嗓子就倒仓了。——几个戏班轮流唱,赶场,太累了,又没有休息时间。
原来是顶梁柱,铜锤花脸。嗓子没了,铜锤唱不了了,改架子花,等于改了行当。来什么戏?任志秋(志兴成科班出身,志兴成科班解散后并入文林社)唱《鸿霓关》,我来辛文礼。胡少安唱《珠帘寨》(又名《解宝收威》),我来周德威。还来过《取金陵》的赤福寿等等,不唱铜锤了,戏也没多少了。
好容易有点意思了,又倒仓了。父亲一瞧,大失所望:“你还是跟我磨眼镜吧。”眼镜我是绝对不磨的,我还是想唱戏,我还是喊嗓子。
我有个磕头把兄弟叫马子明,马子明唱老生,我和他一块喊嗓子。几年前在陶然亭,十来个一块冲金少山喊的,也有他。
我不仅和马子明一块喊嗓子,有时还给他吊嗓子。他是武生马德成的侄子,就住在马德成家里,我管马德成叫干爹。
干爹和裘盛戎唱过《连环套》。70多了,一张口就是正工调,我也给他吊嗓子。他非常喜欢我,演出时不找别人,就让我上台拉了,拉了《剑峰山》、《请宋灵》、《独木关》……
我为什么学拉胡琴呢?这里面有个缘故——
有一次,我上颐和园玩,回来后因为天热,就躺在院子里的一张大石桌上睡着了,结果受了凉。醒来后,嗓子没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把我急的。晚上还要唱《探阴山》呢!父亲赶紧请大夫,大夫说:“买七个藏青果和两个松花蛋熬了,吃了。”那叫一个难吃!吃完后休息,起来后“咿——啊——”出来点声音了,吃了点东西,就去三庆演出了。
我没私房胡琴,用的是官中胡琴,胡德泉给我吊嗓子,我说:“胡大爷,今儿您给我降点儿调门,我的嗓子……”“我这胡琴不能落。”官中胡琴,他不想来回地折腾。当时我的汗就下来了!过去唱戏,得有正工调的嗓子才能搭班。胡琴响了,调门挺高,我嗓子上不去啊。就这么唱的《探阴山》,幸亏没得倒好。回来我就琢磨,拉胡琴的怎么这么厉害,不给你降调门!
我家有一把胡琴,我试着拉调门,找着了。过门不会,我家离花市挺近的,就隔一条胡同,就跑到花市义和祥店铺去听。义和祥店铺天天都放京剧唱片,有梅兰芳的、马连良的。听完后捂着耳朵再往回跑,到家就找那音儿,找到了。
见我嗓子倒仓了,干爹就说:“你这嗓子已经倒了,再想练出来就难了。你不是会拉胡琴吗?你改拉胡琴准行,你手音好。”
改拉胡琴后,我上哪练去?花市有一洋市口,洋市口里头有一茶馆,茶馆名叫青山居,掌柜的姓孙。原来的“和声雅韵”票房搬这儿了,社长朱少峰,唱花脸的;副社长姚正平是宣武医院的院长,弹月琴;儿子姚照林拉胡琴。票房每天都有戏,请的尽是好角儿,侯喜瑞、马德成、王仲林、奚啸伯,这都是内行,也上这票房唱去。
票房里有我的把兄弟,一个叫郭叔良,一个叫杨又堂,一个叫张连鹏,一个叫穆玉秀。我们拜把子,也不吃饭,也不磕头,谁岁数大叫大爷,谁岁数小叫小爷。大爷穆玉秀,唱旦角;二爷张连鹏,唱老生;三爷郭叔良也是唱老生的;四爷杨又堂唱丑角,也是票房的总管,就让我上那儿去。
我那时是官中胡琴,侯喜瑞、马德成都是我拉。还有孙子鸣,唱旦角的;龚云甫,唱老旦的。也是我拉。那儿票房挺红火,我每天都去,拿它练琴。朱少锋,又唱花脸又打鼓。他打鼓,侯喜瑞、马德成唱《连环套》,单找我打铙钹。文武场都得灵。
我的这几个把兄弟,现在都没有了。照片还能找出一张,还是黑白的。
我们这几个,跟马三立都特别熟。
张连鹏在天津唱《失•空•斩》,请马三立看戏,他不是天天说相声,说一天隔一天。
马三立真逗,真好玩,我管他叫“牙签”,他管我叫“风干香肠”。侯宝林管他叫三叔。不是随便叫的,有准儿的。
说相声的,还有常宝堃、高德民和徐德贵。
我们还老听曲艺,这边儿听小彩舞,那边儿听刘宝全,赶场。还有白云鹏、张小轩、白凤鸣,这仨人唱不过一女的,这女的叫良小楼,像京剧界孟小冬。都是京韵大鼓,几个把兄弟一块去听。
刘宝全饮场,但是不喝。
小彩舞,那时也漂亮,个子小,可是真会唱。我敬仰她,必上后台。
她原来学过京剧老生,“我个儿太小,就改这个了。”
“改这个好。”
“请教你……”她想在京韵大鼓里加京剧。
我给她说过《俞伯牙摔琴》里的反二黄:“呼一声钟贤弟……”《俞伯牙摔琴》要不了大腔,用在京韵大鼓里不合适,就给改了点儿。
还有一出,《连环计》。里面有四平调,她把它拿过来,我给设计腔调,加慢板、流水,新腔,与京剧很接近。
小彩舞的京韵大鼓真好,原来在北京唱,后来上的天津。史文绣的梅花大鼓,王毓宝的天津时调,我们也听。曲艺借鉴京剧四平调、反二黄、流水等,京剧借鉴天津时调、京韵大鼓的过门。王少卿也爱京韵大鼓,从里面借了好几个好过门,也包括三弦技法,揉京剧里了。二者的乐队有相似的地方。
练来练去,干爹就说了:“拜个老师。”
穆玉秀拜了王幼卿,成了王家门的徒弟,杨又堂拜了萧长华。张连鹏、郭书良两人跟我学。
我是练了不少,可真要改行,必须拜老师。
经励科有个沈子厚,我找到他,说:“我嗓子不灵了,要改行,学拉胡琴,您给我找一个拉胡琴的先生吧!”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
那天,南铁生在三庆戏院唱《宇宙锋》,正赶上杜奎三杜先生拉,沈子厚就带我到后台了:“这是杜先生。”我就给杜先生鞠躬,杜先生说:“能收不能收,我得跟我老师说说,徐先生让我收我就收,徐先生不让我收我就不收。”他是徐兰沅的徒弟。
后来沈子厚又带我去杜先生家,杜先生问我来历,我说:“我原来是文林社唱花脸的,后来搭了大班,现在嗓子倒仓了。”“你会拉胡琴吗?”“会拉。”“拉给我听听。”听完后就说:“明天带你去徐先生家,让徐先生听听。”接着又问:“怕苦不怕?”旋子我都翻了,这有什么?“不怕。”他又让我练了练唢呐、笛子和弹拨乐。
第二天,我们俩骑着车直奔徐先生家,徐先生家前后三层院子,那个阔!谁在那儿?王少楼、萧长华。
萧长华问我:“你不是考富连成的那个吗?”
“我是考过富连成。”
徐先生说:“你拉个小开门吧,少楼你吊吊。”
吊什么?《空城计》。拉完了,徐先生很满意,就对杜先生说:“你就收下这个徒弟吧。”
这一年,我18岁。
拜师以后,之一个拉的是鲜蕊芳,是替杜先生拉的。鲜蕊芳是唱梅派的,杜先生拉梅派拉的少,老拉程派。
鲜蕊芳是艺名,她本名叫陆蕊芳。妹妹叫陆蕊芬,艺名鲜蕊芬。弟弟叫陆松龄。
鲜蕊芳虽然没拜过梅兰芳,可她唱的尽是梅派戏,《金山寺》、《凤还巢》、《宇宙锋》、《祭塔》、《女起解•玉堂春》,我为她拉的多了。
我还为她编了一出《春闺选婿》,把《太真外传》里的唱腔全都揉在里头了,以唱功为主。情节跟张君秋的《诗文会》有点相似,讲的是一个女子到了婚嫁的年龄,父母让她自己选女婿,怎么选?考作诗,终于选中了一个合适的,这人最后得中状元,家里因此改换了门庭。
还有毛世来,我也给他拉。我的胡琴,赵都生的二胡。
这时候,毛世来已经和李世芳、宋德珠、张君秋一起被称作“四小名旦”了。
毛世来人好,戏也好,《红娘》、《红楼二尤》、《得意缘》、《战宛城》、《英杰烈》、《小放牛》、《小上坟》……
我唱戏也搭他的班,不为挣钱,就为看他的戏。那跷功,绝了,还有那扮相。到现在我还想毛世来,台上真好,扮相不得了。
小小姜进才,就爱毛世来。
我、马子明,裴世长是打鼓的,还有詹世普和艾世菊,这两个小花脸在科班时就傍着毛世来唱,后来他挑班,还一直跟着他。我们几个是口盟把兄弟。
那时候,我每天必去一趟老师家,寿日、年节更甭说了。他也不拿我当外人。师奶奶拿我当亲孙子似的,还特别疼我。她做寿,师爷做打卤面,我去了,先给我盛一碗卤尝尝。
我的婚事,还是师奶奶做主定下来的。
女方姓朴,朝鲜族,也在旗,老爷子生在东北,是从那边过来的。
她家住茶食胡同,却在手帕胡同上学。手帕胡同外有个烟摊,卖烟的叫李廷才。朴老爷子没事,老去那儿坐坐,也知道我学戏。朴姑娘的二姐叫玉珍,是个戏迷,经常买票听戏。李廷才就想做我和二姐的介绍人。可是二姐比我大啊,不行。李廷才就说:“她有一四妹,在手帕胡同上学。”四妹上学时天天从我家门口路过,天天都能看见,礼拜天不上学,她也上烟摊那儿,也就熟了。我就叫李廷才介绍了。
我把李廷才说的这事跟老师和师奶奶说了,师奶奶说:“相相去。”我说:“您说行就行。”
开明戏院(珠市口)见的面,坐在一个包厢里,一块儿看戏。她学生打扮,白衬衫黑裙子。看完戏,师奶奶说:“她人不错。”

师奶奶点头了,回去跟老师说。老师也点头了,又跟我妈说,同意了这门亲事。
跟杜先生刚学了不到三个月,鲜蕊芳要上东北,老师去不了,就让我去了。
按照行规,徒弟头几年挣的钱,是要拿出一部分给师父的,但师父不要我的钱,反而把他的大衣送给我御寒。我十分感谢我的师父。
说实话,当时我会的戏太少了,而且很多戏都是现学的,可到东北一拉,反应挺好。
鲜蕊芳结婚了,我又开始傍陈啸秋(有“东北梅兰芳”之称)。我傍着陈啸秋,一直唱到黑河,对面就是苏联。黑河有个西餐厅叫“冰岛”,在那儿吃西餐,烤牛肉。东北的冬天,零下40多度。那儿的人都穿着鹿皮靴,阔,有钱,拿金子和白银赌博。我在那儿买过镏子(戒指)。
1942年在东北,除了陈啸秋,我还傍过宋玉声、方荣翔、郑万年(李多奎的学生,唱老旦的)、魏德春,一人傍好几个。
·END·
 杭州办公楼商业租赁信息网
杭州办公楼商业租赁信息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