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铺起名字大全集(店铺起名大全2020最新版的)
点击蓝字 · 关注我们
论清代西方人对中国剧场的认知
廖琳达廖奔
内容摘要:
清代西方人带着固定的剧场概念进入中国,体验了中国戏曲多样的演出场所,分别发表看法,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经历了一场跨文化理解的歧义碰撞和论辩,逐步理清头绪。笔者从搜集西方文献之一手材料(包括文字和图片)出发,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反观戏曲的文化性格和中国戏园特质,也为中国剧场演进史补充认识资料。
关键词:
西方剧场观 认知 中国戏园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1)05-0018-09
廖琳达,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中国戏剧研究。曾在《戏剧》、《戏曲艺术》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廖奔,中央戏剧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博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后。出版著作《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等三十余种,发表论文、散文、杂文、诗歌、剧本、词赋六七百篇,主编“蓦然回首丛书”等数十种。有京剧《胡笳十八拍》、话剧《韩信》、舞剧《金孔雀》等上演。先后获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田汉戏剧理论奖等奖项。
导语
莎士比亚时期的西方与中国旧式演剧环境接近,剧场形式比较随意,街头演出、旅馆剧院、露天伸出式舞台常见。但随着戏剧日益朝向写实发展,也随着剧场艺术领域建筑景观、仿真布景与机械舞台设备等技术、艺术手段的日益成熟,18世纪欧洲剧场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随后远东贸易迅速展开,西方人进入中国看戏的机会日益增多,仍然处于形制不确定和结构多样化阶段的中国戏园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开始记录和加以论说。
中国地域广袤,南北民俗区别很大,就演戏情形来说,京都、城市、乡镇、家庭各自不同,因而剧场建筑也发展不一,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直发生变化。我们今天知道的清代剧场,有戏园、庙台、家台、临时搭台等多种形式。清代进入中国的西方人,脑中带着关于西方剧场的固定概念,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体验了中国不同的演出场所,分别发表看法,于是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甚至互相争论,经历了一场跨文化理解的歧义论辩,才逐步理清头绪。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的文化性格和戏曲特质。
一
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 从1760年开始,在清宫担任机械师、画师、园艺师长达20年之久。他平日留心北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艺术与民俗,因而了解许多戏曲文化。韩国英曾在《论中国语言》一文里指责中国人轻视戏剧,说“他们野蛮地把公共剧院和妓院一样限制在城市之外,而且说是允许它存在,其实只是容忍。”[1] 北京的公共剧院出现于清初,事实上是酒楼戏园,康熙年间(1662—1722年)知名的有太平园、碧山堂、白云楼、四宜园、查家楼、月明楼、金陵楼等。[2] 由于北京内城只准旗人居住,怕他们贪图腐化堕落丧志,清廷屡屡颁布禁令不许在内城开设戏园。如清延煦等编《台规》卷二十五载:“康熙十年又议准,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禁止。”[3] 因此韩国英看到的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情形,北京戏园确实集中在南城墙的正阳门(前门)之外,《台规》卷二十五还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时“前门外戏园酒馆倍多于前”[4],说明了这种情况。乾隆末北京演戏的茶园知道名字的有8座:万家楼、广和楼、裕兴园、长春园、同庆园、中和园、庆丰园、庆乐园,见于崇文门外精忠庙乾隆五十七年(1792)《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这些都是固定的公共剧院。但这种固定的戏园集中在北京、盛京(沈阳)等都城里,成为京都繁华一景,其他地方还没有普及开来,因而在当时不是普遍现象。
于是我们就看到1817年英国戏曲研究家戴维斯(John F. Davis,1795-1890)在他的《中国戏剧简论》一文里反驳韩国英说:“这个说法肯定是假的,事实上中国根本就没有公共剧院。中国剧团可以随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建造出一座戏台:用竹竿作柱子来支撑当作屋顶的棚子,用木板铺成高出地面六、七英尺的台面,台子的三个侧面都用绘有图案的布幔遮住,前面则完全敞开——这就是建造一个中国戏台需要的全部材料。完成的戏台很像巴塞洛缪集市(在伦敦老街区)上为相似目的而搭建的摊位,但远没有那么牢固。事实上,一个普通住宅就满足了演出中国戏的全部必要条件。”[5] 戴维斯的说法还可以从早他半个世纪的英国人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的文章里得到印证。珀西倾心中国文化,他在《1719年广州上演的一部中国戏的故事梗概》编者按中说:“我们发现这里没有任何正规的剧院。”[6] 伦敦《每季评论》1817年10月号在评论戴维斯译本《老生儿》时沿袭了戴维斯的说法:“他们也没有任何永久性的剧院。用到处都在使用的现成的竹子、几块席子和一些印花布,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搭起一个戏台,或者一个带有出口和入口的房间,就足够满足需求了。”[7] 说中国人用竹竿席棚能够迅速搭起一座戏园,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但不能以此否定当时中国另有固定建筑的戏园,这是戴维斯的误解。韩国英长居北京,所说为实。戴维斯因为住在广州,那里当时确实只有临时搭台的戏曲演出,所以产生了盲人摸象的认识。
事实上京都之外,清代前期东南一带也有固定建筑的戏园出现。例如苏州在雍正时期(1723—1735年)已经有了之一座戏园——郭园,乾隆年间增加到数十处。大约在嘉庆年间,扬州也效法苏州,开设戏园,有固乐园、丰乐园、阳春园等出现。上海在咸丰以前(1851年以前)也模仿苏州戏园创建了张家花园,也是戏园。[8] 这种底层民众聚集喧闹的地方,西方人很少去,所以他们见不到这些戏园演出。
但是,因为戴维斯的权威性——他长期生活在中国,最早翻译了一批中国小说戏曲文本(包括《三与楼》《好逑传》《老生儿》《汉宫秋》等),是英国研究中国小说戏曲的开山祖,后来又担任了香港总督,加封爵士,具有一定声望,因而他的见闻录长期误导了西方读者。即使是后来进入中国的旅行者和传教士,也因为所游历地域的局限,得到和戴维斯同样的片面认识。长期在福州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 1866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说:“(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专门为演戏而建造的剧院。每座寺庙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在方便的地方建一个戏台,专门用来演戏。这座城市(指福州)以及它的郊区有几百座这样的寺庙。为了演戏,晚上也经常在街上临时搭台,白天很少。这种街头戏对旅行者和从事货物运输的人来说总是受欢迎的。戏班也经常被雇佣在富人家里和官员府邸演出。”[9] 长期在山东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 1868 年出版的《中国和中国人》一书也说:“中国没有专为演戏建的固定性大剧院,演出在庙宇、私宅、街道和路边进行。各种庙宇的神像前都有一个戏台或平台,专门为演戏而建造。富裕家庭会在大的内院里搭建临时戏台。有时一家或几家联合在附近空地上搭建一个戏台。在商业街道上,为了商贸繁荣常常在店铺前面演戏,这时戏台就会跨街而建,它的台面非常高以便路人穿行。”[10] 他们都谈及了中国演戏的几种场合,但结论是一样的:中国没有专门演戏的固定剧院。如果说清代的酒馆和茶园剧院兼营茶酒,不算专门演戏的剧院,出自西方纯粹艺术观,也有他的道理。但对中国人来说,它们就是专门演戏的固定戏园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清代史料里,都把北京茶园直呼为“戏园”可证。但卢公明、倪维思都没有见到过。
倒是有许多西方人注意到,中国固定建筑的戏台是普遍存在的——即遍及中国的神庙戏台。只是它们并非专为演戏而设,主要用于酬神活动,与欧洲剧院的世俗性功能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卢公明说:“演戏经常是一种崇拜行为,通常用于重要的节日庆祝活动。戏剧演出通常与感谢神明联系在一起……戏剧与中国人的节日庆典密切相关,与在神灵面前进行宗教崇拜密切相关……在很多情况下,戏剧表演被认为是一种仪式或崇拜的一部分。”[11] 倪维思也说:“中国戏剧公开宣称的目的也是其主要目的是尊崇和抚慰神明,这些神明通常以塑像、牌匾和版刻的形象出现,摆放在最为尊贵显赫的位置。”[12] 除了功能不一样外,神庙戏台的演出环境当然也和西式剧院大相径庭。
到了清代后期,或许受到京都戏园或者西式剧院的影响,广东一带才逐渐建起固定戏园。1899年英国人斯坦顿(William J. Stanton)在《中国戏本》一书里说:“在香港、澳门、广州和其他一两个地方,建有很大的戏园。戏园后部有固定的戏台,上面绘着美丽的图画,但画的内容与演的戏没有关系。”“在香港固定建筑的戏园里,每天演出两次。从上午11点开始,黄昏时稍作休息,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13] 当然这种戏园是中式的,与西方剧院不同。法国画家博尔热(Auguste Borget,1808—1877)1838到1839年间曾到中国游历,画了许多写生图,其中就有固定的戏园。后来他为法国作家老尼克1845年出版的《开放的中华》[14] 一书绘制插图211幅,其中有戏曲场景四五幅,就包括一幅固定的戏园画。 (图一)图中正面为高高的戏台,上面有至少10个演员正在演出。两侧环楼有二层看台,观众挤坐,还有孩子坐在栏杆外面甚至攀到顶层。中间是普通观众拥挤站立的池子,台前看到有一成人托着孩子往戏台上爬。顶部未绘出,但拉有横铁杆,悬有7个宫灯。其建筑形制与当时普遍见于神庙的戏园相仿,只是戏台对面没有神殿而是看台(图中未绘出)。
图一:博尔热绘“泉通中国老街戏园”(1845)
二
西方剧场文艺复兴时期也和中国差不多,有众多的客厅剧院、街头临时搭台演戏等。但18世纪西方剧场已经发展为固定的建筑样式,其基本结构为平面马蹄形的楼厦,配以华丽的廊柱和雕塑,内部一头是箱形舞台、镜框式台口,舞台上的梁架上安装了悬挂帘幕布景和特技设备用的滑轮、绞车、杠杆等,并设置了天桥,舞台后部通向演员宽敞的化妆室。观众厅分为池座和楼座或包厢,设置了中间带过道的横排沙发式或木制座椅,天顶悬挂着玲珑晶莹的烛架和吊灯。观赏大厅外还有配套齐全的门厅和侧厅用作休息厅,体现了一种崭新的空间观念和观众意识。习惯于在这种剧场里看戏的西方人,遇到简陋的中国戏园,自然会产生许多不适应。
英国传教士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1799-1845)1841年出版的《中国人的戏剧娱乐》一书说:“中国人建筑设计的理念很差,因此不会建造那种能够满足公共剧院要求的名副其实的建筑。”[15]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1899年出版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也说:“除了个别大城市以外,中国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有座位、用屋顶和墙围在里面的剧院。”[16] 英国学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里说:“这些戏台基本上都一样,没有幕布,没有吊杆,没有侧厅。”[17]
事实上清代后期中国戏园虽然参照了西式剧场,但仍然与之不同,即使是在美国唐人街建的戏园亦是如此。1852年曾有一个叫“鸿福堂”(Hong Took Tong)的中国戏班从香港到旧金山为华工演出获得成功,不久就在杜邦街(Dupont Street)——今天的格兰特大道 (Grant Avenue)建造了一个千人座的中国戏园,地板前低后高,没有包厢和休息厅,顶部挂有22盏宫灯,戏台前有一个能装40位乐师的乐池。[18] 由此可见这座经过改革的中国戏园,仍然大体保持了中国的传统式样,只是增设了乐池,让乐队从戏台后部搬到了前面的乐池里,并将观众隔得稍远了一些。我们今天可以见到一幅1879年前绘制的旧金山杰克逊街华人戏馆兴春园演戏图 (图二)[19],大体反映出改良戏园的内部模样:一座封闭式大厅里,戏台设于一侧,带有半圆台唇,台后仍然保留左右出将入相两个上下场门,悬着门帘。画的视点是从环形二层看楼后面望过去,可以看到许多戴礼帽的中国观众一排排挤坐在二楼观看演出。
图二:旧金山华人戏馆兴春园绘刻(1879)
西方人在中国广泛注意到的演戏场合,分别为堂会戏台、神庙戏台和临时戏台演戏三种情况。让我们分别来看看他们的关注点。
堂会演戏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普遍现象,是家庭私宴或官厅公宴的配套演出,明代耶稣会人士入华时就留下了相关记载。正如戴维斯所说:“中国……多数大宅门里都有专门用于演戏的大厅。”[20] 法国作家老尼克道光十六年(1836)来到广州,曾到泰顺行的行商马佐良家赴宴看戏,又为广东巡抚林琛的女儿做手术治好白内障,应邀赴宴时在林家观看《窦娥冤》《补缸》等戏,并亲眼目睹了开戏前去搭建的全部情形,记载于1845年出版的专著《开放的中华》一书中。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还收有画家博尔热画的一幅宴会演戏插图,图的左前方绘有官员家庭设宴情形,右后方绘有一座戏台,上面6个演员正在演出,恰为实景。 (图三)
图三:博尔热绘堂会演戏图
神庙戏台由于有看廊、看楼和庙院配套,就更加接近固定建筑的戏园,只是露天不封顶。1846年被清廷从内地递解澳门,从而有了从四川经湖北、江西到广东旅行经历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Huc, 1813-1860),1854出版《 *** 》一书,就把这种庙台直接称之为戏园。他说:“(中国)到处都有戏园子。大的市镇里遍布,演员们白天黑夜地演出。没有哪一个村子没有戏园。戏园子通常建在寺庙的对面,有时干脆就是寺庙的组成部分。”[21] 有一次,因为客栈住满了,遣送他的清朝官员甚至就安排他在这样一个戏台上铺床睡了一夜,他因此有着对庙台环境的真切体验。前面提到的倪维思也说:“各种庙宇的神像前都有一个戏台或平台,专门为演戏而建造。”[22] 卢公明也说:“每座寺庙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在方便的地方搭一个戏台,专门用来演戏。这座城市里以及它的郊区有几百座这样的寺庙。”[23] 还有一个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也在他1896年出版的《中国一个甲子》一书里说:“每座庙宇都在神像的正前方建有一个戏台,戏主要是演给神看的。但就像为神像供奉的祭品事实上给人们提供了一场盛宴一样,演给神像的戏也免费供应给了大众。因为庙里很少有座位,观众都站着看戏。因此,他们是不是在听戏,一方面取决于戏班的吸引力,一方面也取决于他们肌肉的耐力。”[24] 丁韪良注意到了这种看戏环境对于观众肌肉持续力的要求,意思是中国戏园从不考虑观众看戏的舒适度。
古伯察还生动描写了这种戏园的嘈杂演出环境:“观众总是呆在露天地里,他们的位置没有确定的限制。每个人都能找到他自己更好的位子,街道、房顶甚至大树上,可以想见其喧嚣与混乱。所有的观众都尽情吃、喝、抽烟、谈话,兜售吃食的小贩在人群中穿梭。当演员在公众面前倾尽全力再现伟大的历史与悲剧事件时,这些小贩扯着嗓子在叫卖他匣子里的南瓜子、甘蔗糖、炸红薯和其他美食。”[25] 但是这种民俗环境却恰恰是中国演戏与西方观念不同的结果,中国人是把它当作盛大节庆的红火热闹场所看待的。我们从清代刘阆春所绘《农村演戏图》 (图四)里,恰看到古伯察所描写的情景,二者可以互相印证。
图四:清刘阆春《农村演戏图》
戴维斯提到的临时搭建戏台,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西方人入华都十分关注并注意记录的民俗。例如倪维思就说:“有时一家或几家联合在附近空地上搭建一个戏台。在商业街道上,为了商贸繁荣常常在店铺前面演戏,这时戏台就会跨街而建,它的台面非常高以便路人穿行。”[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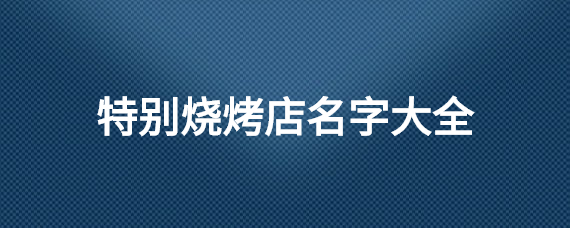
正如戴维斯说的,中国人可以随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建造出一座戏台。老尼克1836年在广东巡抚林琛家里赴宴看戏,就亲眼见到了这种临时戏台的迅速搭建:“在宴会厅的窗台前,匆匆用竹竿搭了一个六七尺高的戏台,三面用红幕布遮挡,只在戏台的后面给演员们留出一小块后台,用一块大帘子隔开。留下两扇门:左边一扇为进口,右边一扇为出口。”[27] 1847至1859年在中国经商的英国人斯卡斯(John Scarth)喜欢钻进戏园后台,观察演员化妆,和演员交朋友,也喜欢画速写,给演员画像。他1860年出版的《在华十二年》[28] 一书里,收有他画的一幅临时戏台图 (图五),恰是一座最简陋戏台的演戏场景。图中戏台仅仅用几根竹竿挑起帷幕,围成一个前面开口的四围空间,6个演员就在台面上表演,观众挤着站在台前地坪上观看。想来搭建这样一座戏台确实不需要几个时辰。
图五:斯卡斯《在华十二年》临时戏台图
三
由于演戏和搭设临时戏台的需求量极大,18世纪后期在商业都市里就逐渐出现了专营商铺。例如演戏订戏班,吃席定戏筵,搭戏台请搭台行,各有分工又各有专工,形成了一条龙服务,对客户来说极其便利。陈雅新在大英博物馆所藏清代广州外销画所绘广州十三行商铺里,找到了3个戏筵铺和1个搭戏台铺的绘画。[29] 其中戏筵铺“集和馆”“品芳斋”“龙和馆”的招幌上都写有“包办荤素戏筵酒席”的字样。包办酒席自然不止是戏筵酒席,不演戏只吃席的客户也应在经营服务的范围之内,但当时几乎无筵不戏、无戏不成筵,所以这些酒店就都把“戏筵酒席”直接标在了招牌上。搭戏台铺二招幌上一书“李号承接各乡醮务戏台蓬厂”、另一书“承接花草人物戏台主固不误”字样,画中于门旁绘有竹竿、木板、席筒等搭材,门内亦有匠人手抱木板出入。这些说明了此铺的经营业务:为城乡祭神活动搭建棚木结构戏台,并承诺按时保质完成。19世纪末有西方画家画出这类戏台的结构草图,可以参考。 (图六)[30]
图六:19世纪末西人所绘戏园结构图
旧时中国的剧场空间不大考虑普通观众的安置,通常在村落空地或街道上临时搭起一座戏台即可演戏,普通观众则随意散乱观看。但一般也还要在戏台对面、侧面搭建“女棚”“看棚”,供身份特殊的女性和士绅使用。我们在明清戏画里经常见到这种观戏环境的描画。斯坦顿描写过这种情况:“高大的戏院以惊人的速度竖立起来,完工后,它们相当舒适。常见样式是一座高耸的金字塔形中心建筑,一头是戏台和化妆室,两侧和对面都有搭起来的看台提供座位,它们围着的中间部分没有座位,那些免费进场的观众站着看戏。”[31]
这类戏园虽然已经比较完备,终究不像西方剧院那样重视观众席的设置,即使是在看棚里,也达不到相对的舒适度。一些喜欢在中国钻研戏园的西方人,就不得不承受观剧之苦。李太郭曾经买票进戏园长时间看戏,顺木梯爬上看棚,挤坐在中国人堆里,一度引起了骚乱,下面多人看到外国人,都爬上来和他搭话,被管理人员和警察赶走。他描写自己的感受说:“演出持续了大约六个小时,从来没有休息过,但是演员和观众都对演出如此投入,没人觉得疲倦。冒着炎热的天气,在一个硬板凳上坐了这么久,当服务员最后取下节目板时,我感到很高兴。”[32]
这类临时戏园逐渐把“女棚”“看棚”连接成整体看台,就接近了当时茶园剧场的结构,但还是露天的。李太郭具体描述了这类戏园的建筑样式:“他们演戏的建筑是临时性的,就像田野里搭的帐篷一样,一旦演员和聘请方签好了合同,就会立即搭建起来。它们的规模差别很大,虽然使用的设计图几乎相同,一般由四个独立的建筑组成,围在一个四围空间的四面。一面是戏台,仅仅由一个供演员使用的化妆室和平台组成。它的对面是一个专门供妇女看戏用的看棚,正对着戏台,体现了中国人对妇女的特别照顾,因为正前方是最有利的看戏位置,而在看棚里陌生人几乎看不到她们……两边的侧棚是给那些付钱买座的绅士们准备的,而中间圈围的场地里则挤满了各个阶层的人,他们免费入场。”[33] 从李太郭的笔下,我们不难看到,19世纪中期的中国临时戏园也比较完善了。
但这种临时架设的棚木结构戏园,更大的风险就是火灾。由于中国戏园里的乱象:点油灯、抽烟、放爆竹甚至油炸小吃,稍有不慎会使之化为灰烬。斯坦顿《中国戏本》里留下一次骇人记载:“对这种易燃的建筑来说,火灾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经常放爆竹,而且晚上里面的大油灯也一直亮着。曾发生过一些与之相关的令人震惊的火灾,烧死了好多人……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发生于1845年5月25日,在广州的科考试院里举办一场纪念华佗诞辰的演出。周围都是临时搭建的拥挤的棚架,当警报响起时,一个出口碰巧被锁上了。大火迅速蔓延,有两千多人丧生。场景非常可怕,整个封闭区域都被尸体覆盖了。一些地方的尸体摞在一起,另一些地方只有一堆堆灰烬代表着那些曾经充满活力和欢乐的人。有一个地方,人挤得密密麻麻,虽然被烧死了,尸体仍然肩并肩地站着。几年以前,在Ko-iu区的Kam-li,一个棚木结构的戏院因纵火发生火灾,数百名观众和大多数演员被烧死。”[34] 让人如此毛骨悚然的事故,类似记载我们却从未在中国史料里见到过。是轻视人命还是习以为常见惯不怪?抑或演戏之事不登大雅之堂不足道哉?西方剧场的消防设施在这里更是无从提起。
1901年美国学者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学史》,其中谈戏曲部分总结了中国戏园的四种形式,应该说认识比较全面了,引述于此:“在中国的大城市里,除了新年的一个月和为死去的皇帝服丧期以外,戏剧全年都在公共剧院里上演。进场不买门票,但所有观众都必须买吃食点心。各行各业的商业行会也都在他们的会馆里建有戏台,定期向所有站在露天庭院里观看的人提供免费演出。官员和有钱人通常把演员请到他们的私宅里来演出,一般是在举行晚宴时演戏。农村则在庙宇戏台或道路上搭建的临时戏台上演戏,演出由公众摊付费用。”[35] 其中所说的会馆戏台实际上和神庙戏台性质相同,因为会馆也都是敬神之所。总之,西方人对于中国随意而复杂又不断变化的各类剧场形式,有一个长期的感知过程,从他们的记叙里,也透示出中国古代戏园的特色及其缺陷,为我们今天的认知提供反思。
参考文献:
[1] Cibot Pierre-Martial,“De la langue chinoise,”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ékin, Tome Huitieme (1782), 228.
[2] 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9—81页。
[3] 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4页。
[4] 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45页。
[5] J.F. Davis, “A Brief View of Chinese Drama and of the Theatrical Exhibitions”,Laou-seng-urh 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 (London: John Murray, 1817), x.
[6] Thomas Percy, “The Argument or Story of a Chinese Play Acted at Canton in the Year M.DCC.XIX.”, 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 (London: Dodsley, 1761), vol.4 , 174.
[7] Author,“Chinese Drama”, The Quarterly Review,xvi (1817), 406.
[8] 参见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81—83页。
[9]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London: Sampson Low, Son, & Marston, Milton House, 1866), vol.II, 295-296.
[10] John L.Nevius, 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ark: Harper & Brothers, 1868), 269.
[11] Justus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II, 298.
[12] Nevius, China and the Chinese, 269.
[13] William J.Stanton, The Chinese Drama (Hongkong: Printed by Kelly and Walsh, 1899), 3-5.
[14] Old Nick, La Chine ouverte (Paris: H. Fournier, éditeur, 1845).
[15] George Tradescant Lay, The Chinese as They Are (London: William Ball & Co., 1841), 106.
[16] A.H.Smith, Village Life in China (Edi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and Ferrier, 1899), 55.
[17] Herbert Allen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 258.
[18] 程美宝:《清末粤商所建戏园及戏院管窥》,《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19] Henry T Williams and Frederick E Shearer, The Pacific Tourist (New York:Nabu Press, 1879),322.
[20] Davis, “A Brief View of Chinese Drama and of the Theatrical Exhibitions”, ix.
[21] évariste Régis Huc, L ' empire Chinois (Paris: Librairte de Gaume Freres, 1854), 289.
[22] Nevius, China and the Chinese, 269.
[23] Doolittle,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vol.II, 295-296.
[24] W.A.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Third Edition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0), 72.
[25] Huc, L ' empire Chinois, 292-293.
[26] Nevius, China and the Chinese, 269.
[27] Nick, La Chine ouverte, 286.
[28] John Scarth, Twelve Years in China (Edinburgh: Thomas Constable and Co., 1860).
[29] 陈雅新:《西方史料中的19世纪岭南竹棚剧场——以图像为中心的考察》,《戏曲研究》,2019年第4期。
[30] 采自杜维廉《中国戏曲史》附图10(William Dolby, A History of Chinese Drama (London: Elek Books Limited, 1976)。
[31] Stanton, The Chinese Drama, 6.
[32] Lay, The Chinese as They Are, 113-114.
[33] Lay, The Chinese as They Are , 106.
[34] Stanton, The Chinese Drama (Hongkong: Printed by Kelly and Walsh, 1899), 6.
[35]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58.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外戏剧经典的跨文化阐释与传播”(20&ZD28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中国作家协会)
关于我们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创刊于1978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以繁荣戏剧研究,推进戏剧教育事业为己任,坚持古今中外兼容、场上案头并重,关注戏剧热点问题、鼓励理论创新,力推新人新作,曾以发起“戏剧观”大讨论为学界所瞩目,又以系统译介国外当代戏剧思潮、及时发表戏剧学最新优质研究成果为学林所推重,是国内最重要的戏剧学学术期刊之一,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投稿须知
《戏剧艺术》是上海戏剧学院主办的学报,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本刊奉行 “理论与实践互动、传统与现代交辉”的学术理念,设有“戏剧理论与批评”“古典戏曲研究”“现代戏曲研究”“中国话剧研究”“表导演艺术研究”“舞台美术研究”“戏剧教育研究”“跨文化戏剧研究”“国外戏剧思潮”“国别戏剧研究”“学术动态”等栏目。为进一步提高本刊质量,欢迎广大作者惠赐 富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的佳作,尤其期盼 关注当前戏剧实践、学理性强的力作。
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力求杜绝种种学术不端现象,务请作者文责自负。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及教育部有关通知,希望作者来稿时标明和做到以下几点:
1.作者简介:姓名及二级工作单位(如,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
2.基金项目:含来源、名称及批准号或项目编号。
3.内容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篇幅为200-300字。
4.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5.注释和参考文献:均采用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格式如下( 参考2019年以来我刊):
(1)注号:用“①、②、③······”。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请注意各注项后的标点符号不要用错):
A.专著:[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B.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第*期。
C.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D.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E.外文版著者、期刊、论文集、报纸等采用 芝加哥格式: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姓在前、名在后,之间用逗号隔开,首字母大写。书名、刊名用斜体。
F.译文正文中首次出现的新的外来名词和术语、新的作家作品名和人名请附英文原文,并用括号括起。
本刊鼓励 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 平易晓畅、言简意赅的文风,希望稿件以1万字左右为宜。论述重大学术问题的论文篇幅可不受此限。本刊投稿邮箱: theatrearts@163.com;暂不采用其他公共投稿系统。务请标明详细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及联系 *** 。请勿一稿多投, 来稿3个月内未收到本刊录用或修改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务必自留底稿。文章一经采用,将通知作者提供定稿电子版以及 身份证号码、开户银行(建行或交行优先)支行、银行卡号码、手机号等信息,以便发放稿酬。
特别声明:本刊从未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若发现类似信息,可视为诈骗行为,向公安机关举报。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站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相关机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欢迎关注
欢迎关注
• *** :史晶
• 责编:俞建村
• 编审:李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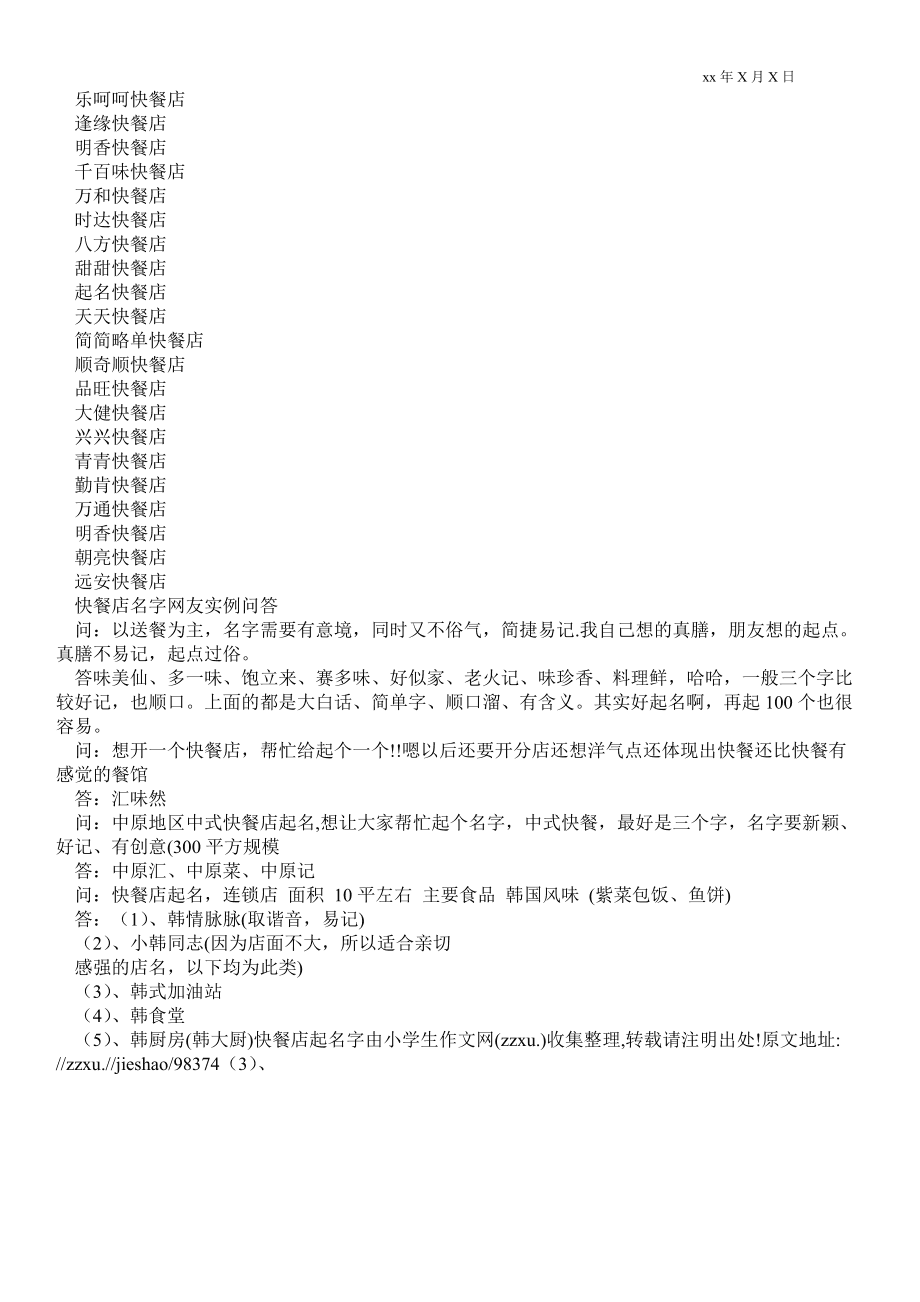
 杭州办公楼商业租赁信息网
杭州办公楼商业租赁信息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