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九画的起名吉利字(十六画的起名吉利字男孩)
论半坡彩陶盆的天象图式
武家璧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摘要:半坡彩陶盆纹饰由口沿纹饰和盆内主体纹饰构成一种天象图式。口沿画“四正四维”宇宙图式,四维“个”字纹与文献相符,四羊纹表示日出入四隅,人面纹源自“二子”相争的故事,演绎为“参商”不相见的星象。参星和商星在春分和秋分点附近,是日月宿舍,两舍中间是冬至点。当二分点位于地平时,冬至点下中天。因此夜半斗柄指东,商星出东方、参星入西方,就是岁首冬至。这是仰韶时代观象授时历历元的特征,西汉《太初历》曾以此历元为“上元”。
中国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彩陶莫过于1955年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作为史前文化的代表,半坡遗址人面鱼纹盆入选中学历史课本。到目前为止,中国共有四处遗址发现了人面鱼纹盆,分别是西安半坡遗址[1]、临潼姜寨遗址[2]、宝鸡北首岭遗址[3]和汉中何家湾遗址[4],都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说明“人面鱼纹”装饰并非偶然现象,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西安半坡》考古报告提出这种纹饰可能与原始氏族崇拜的图腾有关,从此开启了对“人面鱼纹”的内涵与功能的学术讨论,主要有图腾说、水虫图案说、黥面习俗说、神话故事说、渔猎巫术说、图腾丰收说、生殖崇拜说、天文历法说等等[5],可谓歧见叠出,众说纷纭。本文将半坡彩陶盆口沿上的几何图案与盆内的人面动物纹饰结合起来,认为两者组成一种天象图式,反映先民的宇宙观,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解读“人面纹”源自“二子相争”的神话故事,演绎为“参商不相见”的岁首星象,用以象征宇宙天穹并用来观象授时。
01
彩陶盆的纹饰结构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以半坡遗址出土的最为典型,其口沿上分布的八分方位几何图案非常规整并且程式化,为盆内的人面动物纹饰提供了基本框架。其它地点出现的“人面鱼纹”也与口沿上的几何图案相对应,但口沿上呈箭头状的“个”字纹消失,代之以斜线或折角状的几何纹饰,显然是由半坡的八分图案简化而来。故此以半坡彩陶盆为典型例子,来探讨这类纹饰组合的主要内涵和基本功能。
《西安半坡》考古报告公布了三件彩陶盆的完整照片,分别是人面鱼纹盆(P.4691;图一,1)、人面网纹盆(P.4666;图一,2)和四羊纹盆(P.4692;图一,3)。在这三件彩陶盆的口沿上,可以看到将圆周分为八等份的几何性标志符号[6]。
采用图像学的 *** 来观察彩陶盆纹饰组合的结构和分布特征发现:首先,彩陶盆纹饰是由不同的纹饰单元组成的纹饰组合,可分为盆内的主体纹饰和口沿上的边缘装饰两大部分。主体纹饰为人面、鱼纹、网纹和羊纹;边缘纹饰为八分圆周的几何图式,由对称分布且指向中心的四个单直条纹或四组平行条纹,外加四个对称分布且指向中心的箭头状的“个”字纹组成。其次,几何图式的边缘纹饰为主体纹饰提供了一种框架结构,使主体纹饰的某一母题固定地对应边饰的同一符号,如人面及鱼、网纹位于口沿上的直条纹之下,而四羊纹位于口沿上的“个”字纹之下。第三,人面、鱼纹、网纹和羊纹均呈上下或左右两两对称的模式分布。第四,对称的鱼纹可由对称的网纹取代。
如何解释这些观察到的特征以及纹饰的基本功能?笔者认为应该从纹饰的结构去分析其功能。功能主义认为事物的功能决定其形式与结构,并强调各个部分对于整体的功能;结构主义则认为结构决定其功能,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并且认为个体是可以被替代的。可以把彩陶盆的纹饰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一定的结构具有一定的功能,相同或近似的结构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功能。上述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结构与功能的相关性应该是基本共识。鉴于此,根据已知功能的某种结构去比照未知功能的近似相同的结构,就可以认识到后者与前者近似相同的功能。
02
口沿上的宇宙图式
彩陶盆口沿上的八分图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符号系统,首先从此入手分析其结构与功能,可以把盆的口沿看作是一个平面,沿面上的四个直条纹和四个“个”字纹都指向同一个圆心,把直条纹和“个”字纹两两相连,就会在圆面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米”字形,它表示一个圆的八分方位(图二,1),中国传统文献称之为“四正四维”。
可以找到历史时期仍然在沿用的近似相同的结构——“四正四维”,这种结构非常稳定,表现形式相同或相近,有确定的涵义,反映当时人们的宇宙观,因之可以把这类几何图案称为宇宙图式。例如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太一九宫占”盘的背面[7](图二,2),“四正”用大十字交叉形表示,“四维”则由四个箭头式的“个”字纹表示——即在四维线上加四钩组成,此处是九宫占盘的地盘,表示方形的大地,故此没有出现圆形的天穹。在秦汉地平式日晷中有“天圆地方”的结构图式,于是在大地的四维线上加上了四钩(图二,3)。出土的汉代六博棋局图以及大量的“博局纹”铜镜,都可见到四正四维(或四钩)的宇宙图式。典籍记载的“四维”有地维和天维之分,如《淮南子·天文训》载有“天维建元”[8]“天柱折、地维绝”[9]等语。地维方向是固定的,不会随天运转;天维在恒星背景上是固定的,但随天球周日旋转,只有在每一天的开始时刻(夜半子时),天维与地维才完全重合。

日晷和占盘上的图式符号是有确定意义的,表示大地的“四正四维”八个方向。类似地,半坡彩陶盆口沿上的几何图案也应该表示大地的八个方位。然而彩陶盆的口沿是圆形的,按照“天圆地方”的宇宙图式,彩陶盆可以用来表示“天体”(天的形体),即文献记载的“天圆似覆盆”;但不可以表示“地形”(地的形状),因为“地方如棋局”(六博棋局)。翻过来倒扣着的彩陶盆的口沿与地面重合,于是地面上棋局的格式复印在覆盆的环形口沿上,这就是彩陶盆口沿的图案(图二,1)。这个圆环上的图案是截图式的,不是完整的,完整的“格式塔”(gestalt)在大地的格局上。这种天地复合的格局,要求天维与地维必须重合,谓之天地重逢,是夜半子时的天象特征,即《易经》所说的“天地定位”。因此,彩陶盆口沿的几何图案,被特别用来表示夜半子时的天象背景,也表明了天象的历元时刻在夜半子时。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如此稳定的宇宙图式必定在传世文献中有所反映。在结构功能分析之外,更应该把仰韶文化的宇宙图式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寻找符合传统文化的解释。《淮南子·天文训》载“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羊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10]此处用“二绳四钩四维”表示大地方位系统。“四正四维”加上中心又称为“九维八纲”。秦汉式盘、日晷、博局纹上的“四钩”通常小型化或者位于角隅上,加上维线就是“个”字,去掉维线还原为钩形。因此彩陶盆上的“个”字纹应当是表示“四维”的。
03
四维上的“个”字
半坡遗址发现22种刻划符号,一般认为与文字起源有关,探讨半坡符号与文字的联系,也是解释符号功能的一个重要 *** 。关于半坡刻划符号的性质,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就是文字,如郭沫若先生认为半坡符号“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11]。于省吾先生认为半坡符号“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12]。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文字,如裘锡圭先生认为半坡陶器上的记号具有一定意义,后来的汉字吸取了一些这样的记号,但否认这些记号本来就是文字[13]。汪宁生先生认为半坡陶钵口沿上的几何形符号,是制造者或使用者所作的标记,对后世文字有一定影响,但本身绝不是文字[14]。虽然两派意见相左,但都认为半坡符号与文字有密切关系,不排除后来成熟的文字吸取了符号的某些因素。
半坡彩陶盆口沿上的“个”字符号,就被吸收和保留在文字之中,即是后来汉字中的“个”字。文献记载“个”字表示方位的界线。《说文》“个,半竹也。”[15]《史记·货殖列传》“竹竿万个”,《正义》引《释名》“竹曰个”[16],意思是说两“个”字加在一起是“竹”字,所以“个”就是除掉首尾和枝叶的竹竿。竖立竹竿可以作为某一界线,“界”字古写作“介”,《说文》段《注》说“介、界古今字”[17];《尚书·秦誓》“若有一介臣”[18],《礼记·大学》作“一个臣”[19];《左传·襄公八年》“一介行李”[20],即一个行李;成语有“一介武夫”“一介书生”,都是指“一个”。故“个”与“介”相通,彩陶盆上的“个”字等同于“介”字,即四个正方位之间的界限,就是四维。
文献记载在礼制建筑“明堂太庙”中,“个”指九宫中位于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大庙两侧的偏室,分别称为大庙的左个、右个。如《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载“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21]“季春……居青阳右个”[22]。郑玄《注》“明堂旁舍也。”[23]兹将《月令》记载的天子十二月所居“四庙八个”列举如表一[24]。
根据《月令》中的文字叙述,可画出“四庙八个”建筑平面图,相临的左、右半个,加起来合成一个完整的个室,位于整个建筑的四个角隅,太室居中,玄堂宫、明堂宫位于子午方向上,青羊宫、总章宫位于卯酉方向上,是为明堂太庙的“九宫图”(图三)。
“明堂太庙”是周天子的祖庙,中间是太室,四方为太庙,四隅为个室。各庙、室之间原本相通或者只有矮墙相隔,光线是通透明亮的,故此通称为“明堂”。按照礼制习俗,天子每月居一宫而定“明堂位”,共有“十二居室”,因此必须从“九宫”门面中分出十二个方位,才能满足“王礼”的要求,于是四正宫代表四个正方位,四隅室则各自分解为左个、右个两个方位,形成子、丑、寅、卯等十二方位。
根据周礼,天子每月要在明堂太庙举行“告朔”之祭,所居方位有严格规定,因此明堂太庙必须朝向四面八方,是一个缩小了的宇宙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个”室位于四维,可以追溯至仰韶时代的古老传统。作为四正方位分界线的“个”,总是位于角隅的位置上,这与描绘在仰韶文化半坡彩陶盆口沿上的“个”字纹是一脉相承的。
04
角隅上的四羊纹
明确了彩陶盆口沿上的图式符号的象征意义,盆内主体纹饰的涵义就可迎刃而解。宇宙图式用作天象背景,这是很自然的应用,例如人面鱼(网)纹表示“四正”图象(图四,1),四羊纹表示“四维”图象(图四,2)等,略说如下。
先说四羊纹的涵义。《淮南子·天文训》载“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羊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其中东南维和西南维直接称为“常羊”与“背羊”,西北维名为“蹄通”,也可能与羊蹄有关,这种用“羊”来指称四维的 *** ,可以在半坡彩陶盆找到源头。商代著名的四羊方尊,将四个羊头置于四个角隅上,也是继承仰韶文化传统的结果。
为什么用羊而不是别的动物代表四维呢?笔者认为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羊”与“祥”同音,代表吉祥,汉代铜镜铭文中吉祥一词就写作“吉羊”;二是羊角代表方位中的角隅,四羊就可以表示四角。文献记载四维是冬至和夏至的日出和日落方向,无论是方位和日期都是吉祥的象征。
《淮南子·天文训》载:“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25]《论衡·说日篇》曰“今案察五月之时,日出於寅入於戌……冬与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26]《周髀算经》载:“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阳照三,不覆九……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阳照九,不覆三。”[27]又用八卦方位的四维卦来表示说“故冬至……日出巽而入坤……夏至……日出艮而入乾。”
用现代天文学的概念来理解,《周髀》是用地平坐标系的昼弧(阳照)与夜弧(不覆)之比,来表示日出入的方位,即冬至的地平昼弧为(3/12)×360°=90°,夜弧为(9/12)×360°=270°;夏至的地平昼弧为(9/12)×360°=270°,夜弧为(3/12)×360°=90°,从而可以定量地得到日出入方位的准确数值,列如表二。
“日出入四隅”的理念,与人们的直观经验并不符合,因为黄河流域的居民不可能看到太阳正好从大地的45°维线上升出和落入地平。《周髀》使用的“日出”和“日入”概念和平时的理解有所不同[29],古代十二时中有“平旦寅时”“日出卯时”的说法,就是有两个“日出”的概念,后者指日出地平线的时刻,前者指日出之前看到日光的时刻。古人认为只要“日出”了,太阳就藏不住光芒,就能看到日光;因此之一个“日出”指看到太阳光,第二个“日出”才是看到太阳本身。《周髀算经》的“日出寅”实际上是“平旦寅”。现代天文学有“晨昏曚影”和“曙暮光”的概念,与古代的平旦和黄昏相当,表示日出之前和日入之后的可见光时段;而现代的“晨光始”和“昏影终”则相当于古代的“旦始”和“昏终”时刻。
昏终旦始时刻的太阳方位,人眼是看不到的,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古人把“日出入”方位的两个极值定位在四维上,于是就有了《周髀算经》关于“阳照九,不覆三”和“阳照三,不覆九”的推断。现在的问题是:“日出入四维”的假设,是从何时开始的?屈原《天问》曰:“角宿未旦,灵耀安藏?”[30]意思是说太阳寓宿于角隅之时,已经日出了但却不能看到,它究竟藏在哪里呢?《天问》又曰“八柱何当?”指地平上的八个方位,显然“角宿”是指太阳宿于八分方位中的四角。那么有理由推测半坡彩陶盆的四羊纹表示的可能就是最早的“角宿”的意象。
《晋书·天文志》载:“所谓《周髀》者,即盖天之说也。其本庖牺氏立周天历度,其所传则周公受于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把四羊纹彩陶盆的维线方向理解为日出方位,很容易得出地平昼夜弧“阳照九,不覆三”等结论,《周髀》的这套数据源自“庖牺氏”(伏羲氏),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时代是可以相当的。
由以上论述可知,彩陶盆四羊纹可能与日出入四维的观念有关,整体上仍然可以归为宇宙图式,但已经融入了日出入天象,这种图式与天象的结合可称为图式天象或者天象图式。既然已经有了日出入天象的图式表达,那么同时代的人面鱼(网)纹就不可能与太阳相关了,应该从星象出没的图式中去寻找答案。
05
从“二子相争”到“参商不相见”
中国古代星象中明亮的三联星受到特别关注,《诗经》有“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户”[31]的兴叹。著名的“三星”有牛郎三星(天鹰座)、参宿三星(猎户座)、心宿三星(天蝎座)。参三星与心三星隔着天极处在互相对冲的位置,相传由“二子相争”演变而来,有一则关于“二子不相见”的传说故事非常有名,很可能与半坡彩陶盆的人面纹——“二子”图象有关。《左传·昭公元年》载:
左传·昭公元年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32]。
这则故事反映了参星与商星不同时出现的特定现象。唐诗有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即源于这个故事。参星为猎户座的腰带三星,主星是参宿二(εOrionis);商星为天蝎座的心宿三星,主星是心宿二(αScorpio),后者又称为大火星。商星是夏季夜空的明亮三星,参星是冬季夜空的明亮三星,这两组三星一般不会同时出现在夜空。《左传》把这个故事系于五帝时代晚期的帝喾高辛氏,比半坡遗址的年代晚了将近两千年。实际上从“二子相争”演绎为天象“参商不相见”,这个故事的来源可能非常古老,半坡人面鱼纹彩陶盆的天象图式,可能源于这个故事。
参、商两星均位于赤道以南,从南天星图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参星和商星大致与黄极连成一线,天极围绕黄极作小幅度的绕转,无论天极转到哪个位置,都改变不了参、商两星相对于天极互相对望的基本格局(图五)[33],也就是说岁差运动对两星相对位置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从历史到未来,除了有可能短暂共存于东、西方地平附近之外,参星和商星几乎不可能同时升起在同一片天空。
“参商不相见”是从来就有的天象,并非从帝喾高辛氏才开始。仰韶时代的先民面对同一片天空,同样会发现两组“三星”不共戴天的现象,他们最早用彩陶图式记录了这一天象,故事传播的范围局限在半坡类型分布的关中和汉中地区。帝喾时代的疆域更加扩大,人们重新改编了这个故事,“二子”的封地东至商丘,西到大夏,故事传说遍及豫东至晋南的广大地区。
半坡彩陶盆用作瓮棺葬的盖子,瓮棺里埋葬的是未成年人,而彩陶盆里的人面纹也酷似小孩的大头像,称之为“二子”是很合适的。把彩陶盆的主体纹饰放在口沿图式的框架中仔细观察,即把它作为天象图式来审视,发现一些有趣现象:1.“二子”并非正好位于正直方向的连线上,而是右侧人面在线上,左侧人面在线下(图四,1);2.两个大鱼的朝向可能指示天转呈逆时针方向(朝北看),即文献所载“天左转”,又如《左传·襄二十八年》孔颖达《正义》曰:“虫兽在地而有象,在天二十八宿分在四方……皆西首东尾也”[34];3.实际天象东升西落,按大鱼头向分辨,则右侧升于线上的人面头像位于东方,左侧伏于线下的人面头像位于西方;4.根据人面鱼纹的位置和方向,确定口沿上直条纹连线的方向:穿过鱼纹的连线是子午线,穿行于人面上下的连线是卯酉线(图四,1)。综上可知,彩陶盆两大鱼的方向是南北向,两人面的方向是东西向。这正好符合参、商两星一从东方升起、一从西方落下的实际天象。
问题是卯酉线是方向线,它能代表地平线吗?也就是说两个人面纹可能位于卯酉线的左右侧,何以见得是上下方呢?这在盖天说的理论中是允许的,从剖面图来观察甚至是必须的。盖天说认为天穹是一个盖子,与地面相距遥远并且互相平行,天盖永远不会与地面相交甚至延伸到地平面以下;日月星辰附着在天盖上旋转,转入人眼视线范围以内就是“升天”;转出人眼视线范围以外就是“入地”。按照这样的理论,看起来的上下位置,实际上在一个平面内,因此在盖天说的天文图上,卯酉线完全可以代表地平线,并以此作为天象东升西落的标准线。
06
彩陶盆上的岁首星象
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使得所有天象都具有两个周期,即周日旋转和周年运行的周期。当一幅天象被大地方位框定之后,必须能够指出它是哪个季节(或日期)、在什么时刻观测到的天象,这就是历元。前文已经指出半坡彩陶天象的历元时刻在夜半,那么它是什么季节的天象呢?不能凭主观想象或者所谓“科学推算”去妄下结论,必须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答案。
古代天文学的应用除了占星祭祀之外,主要用于历法,我国最早的历法是观象授时历,许多天象用作授时的标准星象记录在案。《夏小正》是传世最早的观象授时历,上古著名的授时星象基本被保留下来。据胡铁珠女士研究,《夏小正》中全部星象的年代是一致的,以节气在月中来计算天象发生的年代,它们均适宜在公元前800年前后使用,误差不出±300年。这些星象大约在夏朝随二十四节气出现在月初,此后沿二十四节气向后移动,在周代与节气同步出现在月中,天文计算的结果表明《夏小正》是一部从夏朝到周代均可使用的历法[35]。节气点从月初到月中移动黄经15°,按照黄经总岁差每78年西退1°计算,须经过15×78=1170年,这大致符合从夏朝到周代的历史间隔。因此《夏历》以立春为岁首,《周历》以冬至为岁首,后者当是适应星象已由节气移至中气而做出的改革。
与本文相关的星象《夏小正》载“正月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36]陈久金先生指出:初昏斗柄向下指向心宿,相当于大火星下中天[37]。就是说当参星上中天的时候,商星大致下中天,这是由于参、商两星互相对冲的位置决定的。此是正月初昏时的天象,那么到了夜半又是怎样的天象呢?由初昏到夜半,时间大约经过1/4天,星象也以北极为中心左转90°,那么参、商两星的相对位置,已由南北对冲转变成东西相望,故此夜半时参星大约在西方地平线附近,商星大致在东方地平线附近;商星升入天空,则参星必然没入地下;斗柄指向东方的心宿(商星),如《鹖冠子·环流篇》所言“斗柄东指,天下皆春”[38]。由此得到该星象的历元在岁首正月。
前文已指出,参、商两星的对冲位置受岁差的影响甚微,因此上述“参中斗悬”的岁首星象由周朝前推3000多年至仰韶时代也大致是正确的,不过节气应由“天下皆春”改为“天下皆冬”,因为岁差原因,周朝立春营室在仰韶时代应是冬至点。作为历元还应有公元纪年的绝对年代,目前尚不能从图象分析中直接得到更多信息以计算天象的历元年代,但可以借鉴半坡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估计天象发生的大致时期。关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年代,先后有夏鼐[39]、安志敏[40]、严文明[41]、巩启明[42]、邵望平[43]、魏京武[44]、石兴邦[45]、戴向明[46]、任式楠[47]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48]等给出半坡类型或半坡文化的年代范围[49],最新研究成果由碳十四年代专家张雪莲、仇士华等提出[50],各家年代结论列如表三。
上述年代结果除了巩启明先生的结论偏晚500~1000年之外,其余的起始年代都十分接近公元前5000年,主要分歧在结束的年代有早晚之分,大致认为半坡类型存在或者延续了500~1000年之久。综合各家意见取其整数,设定半坡类型的年代范围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之间,延续1000年之久,又取其中数公元前4500年为半坡彩陶天象图的参考历元。历元一定是年始、月始、日始,因此默认为正月夜半合朔。彩陶人面纹的口中画有两鱼对口相向的图象,如同汉画像石中两只阳乌对口相向一样,可能是日月合朔于某个星宿的表示。
下面从天象演示软件SkyMap中检索历史星象图,要求为公元前4500年、夜半合朔、商星升出地面、参星伏入地下。得到符合要求的历元是1月23日夜半,地点在黄河流域(N35°、E115°),这时的天象特征是(图六):
1. 太阳下中天——太阳位于营室,方位角为0°,恰好位于正北方;其高度角为-79.1°,接近天底,人眼看不见;
2. 北斗上中天——北斗位于天顶和北极之间,斗柄朝东,指向升出东方地平线的商星(心宿);
3. 参商两不见——商三星的主星心宿二(天蝎座α)在东方地平线以上18.6°,方位东偏南7.7°;参三星的主星参宿二(猎户座ε)在西方地平线以下10.2°,方位西偏南24.1°。
综上所述,太阳下中天是夜半子时,天与地重合,日与月相会,参与商不见,非常符合半坡人面彩陶盆表示的天象。
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太阳黄经恰巧为270°(图六),正好在冬至点上;月亮至此而与太阳合朔,是为“冬至夜半合朔”,这个特殊天象是节气和月份的共同起点,历法上叫做“气朔齐同”,是四分历的蔀首,古代以此作为理想历元。由是,参星和商星被设想为黄道春分点和秋分点附近的坐标框架,是日月运行的宿舍,这两舍的中间是营室,即冬至点所在。当二分点位于地平附近时,冬至点下中天;因此观象授时的标准是:夜半时刻,商星出东方、参星入西方,就是岁首冬至。
那么怎样得到准确的夜半时刻呢?没有证据显示仰韶时代已经出现漏刻等计时仪器,要掌握时间,一般白天测日影,晚上观星象。《夏小正》载“正月初昏……斗柄悬在下”[51],据此用一根垂线对准斗柄,当斗柄垂直向下时,就是“初昏”终止时刻;然后再扯平一根水准线,等待斗柄指东符合水平方向时,就是夜半。这个 *** 相比漏刻既简单又准确,应是原始先民较早掌握的计时 *** ,不过斗柄指向随季节变化,某个标准只能适用于某个季节,不能用来普适地计时。
总之,仰韶时代特定的天象条件为制订观象授时历提供了客观基础,人们运用简单的技术就可以确定岁首星象。后世在岁首星象的基础上再附加一些理想条件就是理想历元——“上元”。理想历元有“朔旦冬至”和“朔夜半冬至”两种选择,无意之中搜索得到了后者,习惯上文献中也把后者称为“夜半朔旦冬至”。这个结果不是事先设定的,而是随机搜索天文软件得到的,是天文计算的结果,它科学地证明半坡彩陶盆的天象图式,反映了历元时代的岁首星象,同时符合“朔夜半冬至”的标准天象,因而可以用来观象授时,制订历法。
07
仰韶时代的历法“上元”
仰韶时期的天象是否被古人提到过?查找文献典籍,可发现汉朝人早已推算过仰韶时代发生的这一天象,并把它作为《太初历》的上元。《史记·历书》载此事曰:
史记·历书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今日顺夏至……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52]。
《汉书·律历志》有更详细的记载:
汉书·律历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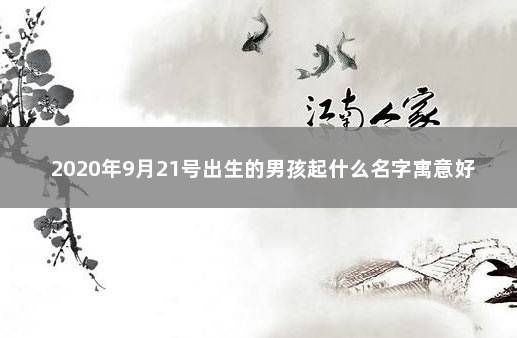
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然则上矣……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乃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53]。
上引汉武帝诏书曰“古者黄帝合而不死”云云,故其所言“前历上元”应是《黄帝历》的历元,而《太初历》的历元为元封七年(前104),距离“上元泰初”4617年,因此理想的“上元”在公元前4721年(4617+104=4721), *** 认为此年是黄帝颁订历法的元年。这完全处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年代范围之内。
4617年是《太初历》一元的周期,它是该历法的章法19、日法81和纪法3的最小公倍数,即:19×81×3=4617(年)。古《四分历》有章法19、日法4、蔀法20、纪法3,其一元周期为:19×4×20×3=4560(年)。古《四分历》制订的年代比《太初历》的年代略早,故前者的上元积年比后者略小一些,实际上它们对“上元”的估计是很接近的。这说明汉武帝时代的人们相信,4600多年前是黄帝时代。
太初改历终结了源自先秦的古四分历,参与者多达二十余人,包括著名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和历法专家邓平,还有历史学家司马迁等一批官员。这次活动给出两个基本结论:4617年前是黄帝时代,标准天象是“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可以说这是一次国家层面组织的断代工程,由于有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倡导和参与,关于黄帝年代的推断,应该不会与当时所能见到的谱牒和年表资料有太大的冲突。半坡彩陶的天象图式的历元年代与汉代推断的黄帝时代非常符合,也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考古学年代互相兼容,距今6700多年,并且得到现代天文学计算的天象与年代的科学印证,从而把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
注 释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第110、111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2] 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12、113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第48、49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陕西西乡何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5] 张云:《半坡遗址三十年研究综述》,《文博》1989年第2期。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图版114、115、117,文物出版社,1963年。
[7]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8]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9]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0] [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第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1] 郭沫若:《古代汉字之辨证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l期。
[12] 于省吾:《关于古代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l973年第2期。
[13]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5年第3期。
[14]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15]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1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6]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3274、3275页,中华书局,1959年。
[17]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8]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二十《秦誓》第5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六十《大学》第10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八年(修订本)》第959页,中华书局,1990年。
[21] a.[秦]吕不韦著,[汉]郑玄注:《吕氏春秋》卷一《孟春纪》第1页,上海书店,1986年;b.[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四《月令》第4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2]a.[秦]吕不韦著,[汉]郑玄注:《吕氏春秋》卷三《季春纪》第23页,上海书店,1986年;b.[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卷十五《月令》第48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3]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第4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个”字下引《礼·月令》注,今本《十三经注疏》无此语。
[24][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四~十七《月令》第456~5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5][汉]刘安等著,[汉]高诱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训》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6][汉]王充著,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注:《论衡》第二册《说日篇》第621、630页,中华书局,1979年。
[27]江晓原、谢筠译注:《周髀算经》卷下第9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28]同[27]。
[29]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第117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30][周]屈原著,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第76页,中华书局,1982年。
[31][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六《唐风·绸缪》第388~3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217、1218页,中华书局,1990年。
[33][法]C.弗拉马里翁著,李珩译:《大众天文学(之一分册)》第42页,科学出版社,1966年。
[34][周]左丘明著、[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0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5]胡铁珠:《〈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6][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卷二《夏小正》第29页,中华书局,1983年。
[37]陈久金:《北斗星斗柄指向考》,《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年第3期。
[38]黄怀信:《鹖冠子校注》卷上《环流篇》第70页,中华书局,2014年。
[39]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40]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考古》1979年第4期。
[41]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42]巩启明:《试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44]魏京武:《碳-14测定年代与陕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4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59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46]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47]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载《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65~81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49]王仁湘:《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关系研究检视》,《文物》2003年第4期。
[50]张雪莲、仇士华等:《仰韶文化年代讨论》,《考古》2013年第11期。
[51]同[36]。
[52][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1260、1261页,中华书局,1959年。
[53][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十一《律历志》第974、975页,中华书局,1962年。
(文章刊于《文博》杂志2020年第三期)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一)——从“头”说起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二)——脂泽粉黛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三)——大唐遗宝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四)——粟特风情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五)——云想衣裳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六)——熠熠铜镜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七)——长安娱乐
从《长安十二时辰》解读大唐风华(八)——玉盘珍馐
彩陶|跟着祖先学制陶,教你称霸陶艺室
彩陶|人面鱼纹盆 子非鱼,却知鱼之乐
玉杂 | 小棍棍的数学大智慧“问君能有几多筹”
金银|唐朝银饼饼的自述,请叫我富贵儿~
青铜 |来自西周的关爱提示:勤洗手 少生病
玉杂|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水晶多曲长杯
杂器| 理科钢铁直男的爆款数学课,速来围观
壁画|您的好友唐墓壁画邀请您:像爱护文物一样爱护动物
金银|穿越千年的绝美头饰
玉杂|隋唐玻璃器:愿你通透 纯净 无瑕
金银|从秦公一号大墓金器一组浅谈秦国金器
青铜 | 龙的自述
青铜|函皇父鼎: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青铜器
青铜器|带你走近秦国的“大橙武”——青铜剑
( 版权所有 转载注明)
 玄机起名网
玄机起名网




发表评论:
◎欢迎参与讨论,请在这里发表您的看法、交流您的观点。